去年,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教授,在《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一书中,石破天惊的指出华夏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英国人、高卢人、古希腊人、巴比伦人、威尔士人等的根源都在大湘西,以及“英语源自大湘西”。
然而,杜建钢的言论一出现,就迎来铺天盖地的嘲讽,杜建钢被扣上“反智”、“文化义和团”、“民粹主义”、“自嗨”等高帽子,甚至某个著名学者告诫学子时,公开以此为反面教材:“像有的‘专家’论证‘英国人和英语起源于湖南’一样,沦为笑谈”。
让人不解的是,当西方宣扬“中华文明西来说”时,当西方声称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时,当西方否定中国5000年文明史时,当西方否定夏朝时,当西方声称古希腊工匠指导秦始皇制作兵马俑时,当英国出土“吉姆在这里”时,当德国出土3300年前寒光闪闪的青铜宝剑时.........没有看到某些人说西方学者“沦为笑谈”,以及“反智”等帽子,偏偏中国学者就“沦为笑谈”了,如此岂非只许西人放火,不许国人点灯?
更为重要的是,从湖南考古发现来说,杜建钢的立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其中之一是湖南发现距今大约万年的字符,比我们熟知的贾湖刻符还要早,比楔形文字早了4000多年,比甲骨文更是早了6000多年,因此有学者认为湖南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字符。

位于湖南常德澧(lǐ)县的“彭头山遗址”,距今9500年—8100年,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四周有壕沟、堆筑的土围和天然河道为护围,以水稻为主粮。
与其他同时代遗址不同的是,学者在研究该遗址棒形坠饰时,发现其中一些上面刻有着极为工整、纤细、端正的字符(详见下图拓本,左为彭头山坠饰,右为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头饰,两者应存在联系),说明并非随意刻写,而是有意为之,必然代表某种特别的含义。
学者刘志一在《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中指出:“可以说,彭头山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古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字符”,如果算上彭头山字符前的草创阶段,那么中国文字显然已有万年历史。
以上图字符来看,不仅字符形态成熟,而且刻写工正、做工精细,显然反映当时刻写技术已经成熟,说明此前有过漫长的积累,不然如何做到这种程度?因此,刘志一推断中国已有万年文字史,一点都不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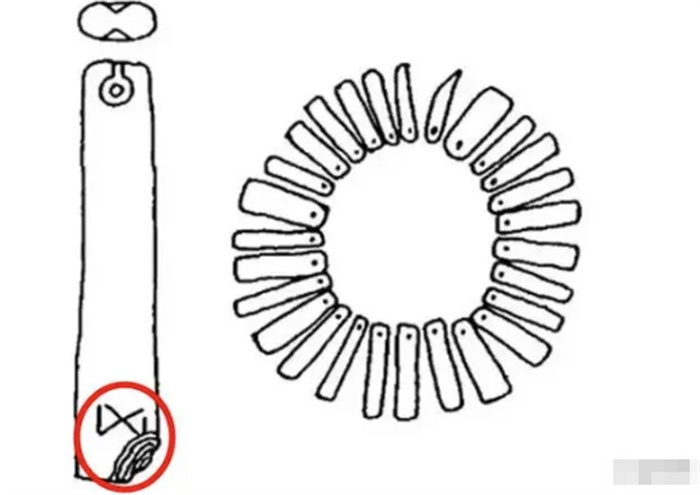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辩驳认为上述符号未必是文字,也可能仅是一种符号,笔者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字符”了。究竟如何,不妨看看下面两个考古发现。
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三峡工程的需要,考古挖掘了湖北宜昌秭归“柳林溪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圆形陶器(见上图),距今7000年以上。学者冯时认为,这是九宫图(洛书)的前身。通过下图可见,其中一个符号与彭头山的一模一样,只是上下各多了一横。
值得一提的是,该陶器上类型“父”字字形的符号,后来也出现在山西陶寺遗址、以及甲骨文中,现代专家将之释读为“文”。
上世纪70年代,在苏州城东南15公里之处,考古发现“澄湖遗址”。该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以及后来的商周、汉晋、唐宋等时代。其中,在良渚文化层发现一件黑皮陶鱼篓形贯耳罐,上面四个符号排成了有序的一列,里面有一个就是上述彭头山刻符,现代学者普遍将之释读为“五”,还有将之释读为“会”。
另外,上图可见的左边第一个符号,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即为权力的象征——斧钺。由于“钺”、“戉”、“越”的最初文字都是“戉”,因此现代学者将之释读为“越”(越人)或“钺”。
至于甲骨文中,上述彭头山刻符的字形被用为“五”,并被一直沿用至今。
显然,彭头山这个刻符在上古极为重要,究竟有何意义,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符号一脉相承至今,而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柳林溪遗址的洛书,还是澄湖刻符,或者甲骨文上的“五”,明显都是文字(数字也是文字),那么上述彭头山符号是不是文字?

可见,彭头山字符的出现,表明中国具有上万年的文字史,比楔形文字、古埃及文等都要早得多。
受宗教思维的影响,西方往往相信“单一起源”,即谁更早谁是起源,比如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文明起源说(苏美尔先后影响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以此逻辑来看,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那么为何不能说楔形文字源于中国,或受中国文字影响等?如此,杜建钢的“华夏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等立论就未必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