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并非来自于殷商王朝的都邑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崭新时代,揭示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殷墟遗址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等丰富文物,为我们呈现了古代文明的三大标志:文字、青铜器、城市。尽管我们在殷墟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王陵,但关于殷商王朝历史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是,殷墟遗址是否完整地代表了殷商文化?这个问题一直是考古学家们的困惑和挑战。著名考古学家刘绪曾在病中向殷墟考古队长、著名考古学家唐际根教授请教:“商王朝为什么叫商?为什么又叫殷商?你考虑过吗?”这个问题成为刘绪教授终生的遗憾。

唐际根教授回忆道:“这个问题,要说没考虑过是假的,但我没有答案。于是回答说不知道。刘老师说他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这是个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研究一辈子商文化,却不知道商王朝为什么称‘商’,终究是遗憾。”(唐际根《何以是“商”朝》)。殷商王朝的历史中,“殷”和“商”的问题,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
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破解这个问题也需要多角度的研究才能揭示深层的历史真相。唐际根教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通过对“商”字象形甲骨文的产生来源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为解决殷商王朝中“殷”与“商”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方向,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商文化的认识,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上世纪初,殷墟遗址的甲骨文和甲骨器物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位于西周王朝起源地的周原也出土了一批甲骨文和甲骨器物,却鲜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周原甲骨文的归属问题,究竟是周氏族还是商氏族的,仍然存在争议。但根据王宇信在《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中的相关论证,我们可以基本得出两个结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属于商王所有,而非周部落本氏族所有;周原甲骨的凿钻形态与殷墟甲骨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并非来自于殷商王朝的都邑殷墟。这引发了一个重大历史谜团,即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和甲骨器物究竟来自何处?它们是否来自于另一个与殷商王朝中殷墟地位同等重要的商人庙祭中心?殷商王朝是否由殷地和商地两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组成?“殷”和“商”是否代表了两个不同地域的称谓?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提到:“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王国维也认同这种说法。(唐际根)。这表明,在殷商王朝时期,使用地名来称呼一个王朝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即使盘庚将都城迁至殷地,将殷地作为新的都城,商王返回商地,进入商王先王商地商都,祭祀先王先庙,这与现代中国人每年清明节回乡祭祖的传统有着共通之处。因此,在殷商王朝的历史发展中,“殷”和“商”作为两个都邑的称谓是毫无疑问的。这反映了一种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客观现象。这种习惯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朝和清朝,仍然延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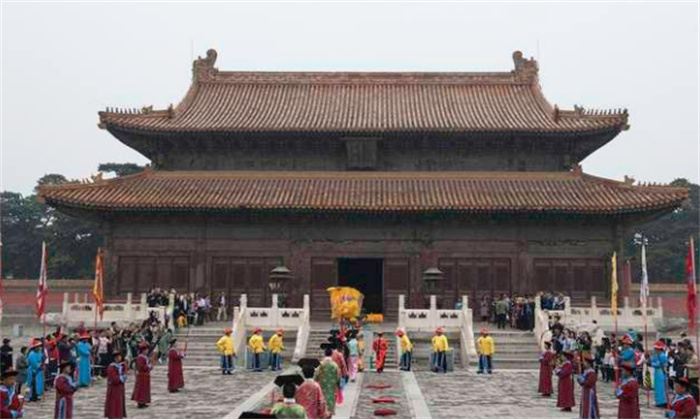
在《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一文中,特别强调了一则周原甲骨卜辞,解释了“贞王翌日乙酉其求称中”的含义。这篇卜辞显示,“贞人”是站在商王立场上占卜的卜者,王就是商王,而不是周文王。这个卜辞涉及到“称中”,这是王建大常颁旗的仪式。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商王典礼的庄重性。同时,周武王灭商后,毁掉了殷都,将其变成一片废墟,保留了大量的甲骨文。他将商地经营成为成周城,作为西周的东方国都。商王朝庙祭的甲骨文也作为战利品被西周的王公贵族带回周原,这为我们今天能够研究殷商王朝的甲骨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许多历史文化中,“商”字被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形文字。它不仅表示击打磬的声音,还象征着一种神圣的庙祭仪式。商字与商人庄严尊敬的庙祭仪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根据《礼记·乐记》的记载,“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这表明,商字与商人庙祭的庄严仪式,是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的。
解开商王朝历史中“殷”和“商”的问题不仅需要多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开放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唐际根教授提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但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更多研究和讨论。只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开放的思维,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揭示其中的历史之谜,还原中华文明的丰富历史。这也是对历史研究者的一种鼓励,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探索,解开历史中的谜题,不让美好的愿望成为终生遗憾。